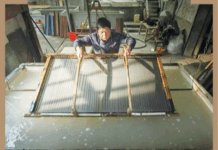法国巴黎里昂火车站的一战华工雕像。本报记者 龚鸣 摄

比利时波普林格一战华工纪念园的纪念雕像。本报记者 任彦 摄
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菲利普·方汉勒米尔斯
一战华工的历史性贡献正逐渐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要记住华工们感人的付出,并在2019年继续讲述一战华工的故事。
在20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巴黎纪念活动上,发生了值得关注的一幕:法国巴黎凯旋门前,一位华裔女孩站在众多世界领导人面前,用汉语朗读了一战亲历者顾杏卿的回忆录里的片段,让人们在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之时听到了代表中国的声音。声音在凯旋门前回荡。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中国在一战战场上的存在。
根据历史资料,顾杏卿是英国军队在中国招募的9万多名劳工之一,加入一战华工队伍时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当时的他认为那是踏出国门、换取美好未来的跳板。顾杏卿最初并无意将自己对战场上的观察、记录和回忆公之于众。直至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才决定将笔记整理出书,希望以华工在欧洲战场的经历勉励同样饱受战争蹂躏、遭受战争苦难的同胞。他相信即使面对看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维护国家的存续和利益。
巴黎和会并没有带来基于平等的和平。大多数一战华工战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一战华工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引起波澜。长期以来,西方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地位,中国的作用和牺牲被边缘化。
直到一战结束几十年后,通过欧洲和中国学者及当地人的共同努力,收集、恢复一战华工故事和史料,一战华工逐渐得到应有的关注。
比利时、法国边境附近的伊普尔小镇在纪念一战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一战期间,伊普尔被三面包围,饱受战争磨难。战后重建的伊普尔镇在新城东门——梅宁门门墙上印刻了成千上万参加一战士兵的名字,华工的名字却被忽略。直到2010年5月28日,一场特别的纪念仪式在这里举行。来自中国的代表向公众宣读了30名失踪华工的名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公开仪式上宣读一战中失踪华工的名字。
2017年,一战华工纪念活动在比利时波普林格举行。根据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记载,1917年11月15日,德军飞机对波普林格近郊布思本村附近的英军营地进行轰炸,致使13名山东籍华工丧生。为了永久纪念一战华工,波普林格市政府从布思本村购买了原英军驻扎的一块营地,建成一战华工纪念园。纪念园里立起一座华工纪念雕像,纪念雕像选址在华工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意在慰藉在此遇难的华工,铭记所有一战华工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战华工留下的书面记录不多,顾杏卿的《欧战工作回忆录》是其中之一。最近,西方公众已经能够读到另一位一战华工孙干的《华工记》。这名来自中国山东的农村教师回到中国后,以个人笔记的形式写下了他的一战经历。2017年,《华工记》首次被翻译成外语。
尽管一战华工的书面记录很少见,但他们留下的其他宝贵资料帮助我们还原了一战华工历史。一些华工返回中国后,仍然使用着他们从欧洲带回的工具;一些华工带回了欧洲的明信片;还有一些华工带回了在欧洲战场上服役时的衣物……这些小物件后来成为打开了解一战华工历史之门的宝贵钥匙。
10多年前,我们在欧洲国家的地图上看不出一战华工的存在,也没有他们来自中国什么地方的任何显示。但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比利时、法国、英国的地图上逐渐标志出一些点,标明一战华工涉足的地方,他们在路上看到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沿着他们的道路追索历史的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点开始连接,并将勾勒出数以万计一战华工个体走出的路线,这也是一条连接西方和中国、跨越几代人命运的路线。
在欧洲,1918年11月11日标志着一战结束,士兵可以返回他们的国家,当地居民逃离战后的废墟。但当时的一战华工仍然从事清理战场、埋葬死者和战后重建等工作。大多数华工在1919年仍然坚守了很多个月,有些人甚至到1920年春天才返回中国与家人团聚。对他们来说,只有当最后一个华工安全地离开前战场时,战争才能算真正结束。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我们要记住华工们感人的付出。2019年,在欧洲这个曾经的战场上,我们将继续讲述一战华工的故事。
(作者为比利时西弗兰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比利时一战华工史专家,中文名为冯浩烈,本报记者车斌采访整理)
绵延一个世纪的记忆
张岩
思绪回到2013年。为了拍摄一战华工纪录片《潜龙之殇:一战中的华工军团》,我和加拿大导演乔丹·帕特森及其团队沿着当时是学生出身的华工翻译顾杏卿的足迹,跨越三大洲,先后在中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地寻找一战华工的墓地和他们的后裔,还原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集体记忆。
记忆一
中国山东是多数华工的家乡,仅由威海出发赴欧的华工大约就有4.4万名,约占当时英国招募华工总数的47%。这里流传着很多华工的故事。一位名叫考文之的华工刚刚结婚不久就应募赴欧。不幸的是,家里的妻子考刘氏并没能等到丈夫归来,等来的却是丈夫病逝欧洲的噩耗。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中写道,华工“欲求生活而反丧失其生命,夫岂余辈初料所及哉”?据考文之的家人称,考文之死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金,甚至没有收到正式的死亡通知。他的妻子至终也未能见到丈夫的墓碑,更不必说与丈夫合葬。
记忆二
当年华工招募基地之一威海,如今已无任何遗迹。但站在华工出发的码头故址,遥望茫茫大海,仍不免让人思绪万千。《远东时报》的一篇文章曾记载了华工出发时的场景:在送别的路上,他们“要和朋友说说话,要买一包香烟,还要掏出一块钱给路边颤抖着的老父亲”。一经离别,悲情开始在不少华工中蔓延。正如华工樊明修所述:“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卖了命,至死不能还家乡!”他们踏上的是一条充满未知和风险的道路,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一条不归路。
记忆三
在加拿大西海岸的维多利亚岛上,曾经有一个威廉姆·海德检疫站。华工经太平洋抵达加拿大后需先到此接受检疫。该遗址目前已成为一所监狱的所在地,平日极少有人往来于此。这里仍然保留着几座华工墓地,表明他们尚未到达目的地或在归途身故。华工王京连的侄子曾听父亲提过四叔王京连,“从小‘当兵’走了,到现在没有信”,当得知四叔葬在加拿大的信息后,他百感交集。
记忆四
搭上横穿加拿大的火车,我们走了整整四天四夜,而当时华工乘车的时间在一周左右(从温哥华到哈利法克斯)。当时英方出于免除人头税(加方当时规定华人入境需缴纳人头税)等因素的考虑,严格限制华工在车上的行动。大卫·利文斯通的父亲哈里·利文斯通是一位华工医生,一路陪华工从中国威海直至法国。在哈里·利文斯通留下的出行日志里,记录了一例华工死亡事件——一位体格强壮的华工在途中因突发心脏病在睡梦中死亡,他的遗体交给了哈利法克斯军事当局。该华工名叫韩廷贞,来自天津,时年21岁。他的家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韩廷贞的下落。正如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中所提,在途中遭遇危险时所想到的“最凄惨”的事情莫过于身没于大海之中,家人还不知情,仍以为他“乘风破浪正在前进中”。
记忆五
在法国西部的拉罗谢尔,我们找到了华工刘得胜的后代。刘的女儿雷勒·玛奇寇具有明显的华人外貌特征,但并不懂中文。她的父亲也从未向她讲过家乡中国江苏的事情。雷勒希望有朝一日找到父亲在中国的亲属,因为根据刘得胜应募华工时的年龄,家中当时应该尚有父母兄弟。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年,一战华工的史迹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角落,有待我们前去发现。还原一战华工的历史记忆,感受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是反思一战教训应该补上的一课。这种伤痛,中国和中国人理解更为深刻。铭记伤痛,奋发图强,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历史不再重演,是我们纪念一战华工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回声
是时候修正记录、正视真相了。100年前,这些勇敢的中国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欧洲,帮助我们应对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之一,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必须向中国劳工和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切的谢意,认可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英国音乐家克莱夫·哈维
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
——法国总统马克龙
中国劳工旅作出的巨大贡献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遗忘,因此在纪念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我们应该提高对他们作出的非凡贡献的认识。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一战华工们为欧洲的自由和重建作出了贡献,他们是从战争通往和平的桥梁。
——比利时波普林格市市长克里斯托弗·德雅盖
在巴黎里昂火车站落成的一战华工雕像,既表达了对一战时期到法参战华工的纪念,也传递出和平的讯息,这样的讯息对世界的当下和未来都十分重要。
——巴黎第十二区区长卡特琳·巴拉蒂—埃尔巴兹
华工是我们一战和当时欧洲历史的重要部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对一战华工心怀感激。
——比利时伊普尔市一战纪念馆馆长
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
《人民日报》(2019年02月01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