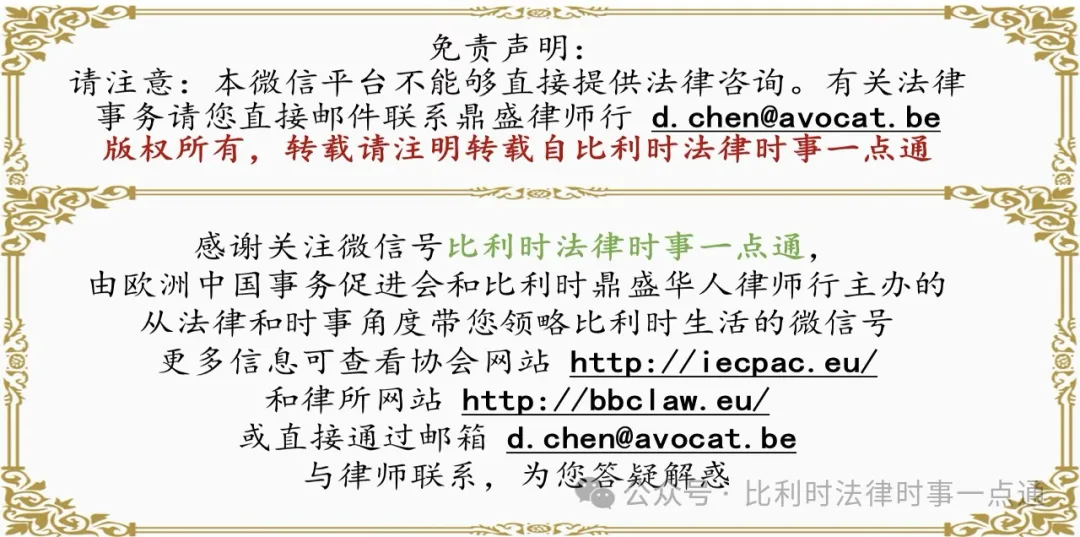作者 Jack CHEN 比利时律师
(曾在乌克兰工作/生活)
个人英文网站:http://avocatchen.eu/
这是我们的“亲历历史随笔 – 乌克兰系列”的第二期。上一期我们聊了身边的乌克兰朋友们对于战争何时会结束的一些私人看法。还没有读过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击这里。有朋友读了我们第一期的乌克兰朋友们非正式访谈录之后,开玩笑说应该也写一期俄罗斯朋友们访谈录。可惜我认识的俄罗斯人很少,不能和大家分享这个不同的视角。当然,更多的读者朋友反馈说对乌克兰东部的情况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以后有空会专门聊一下乌克兰东部,尤其是关于战争起源地顿巴斯地区的一些问题,以及乌克兰朋友们对此的看法。

回比利时之后,身边经常有不少朋友问我,是不是还怀念以前在乌克兰的生活,是不是会回基辅,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工作。心里是很想回乌克兰的,然而考虑到工作,家庭,小孩等各方面因素,短期内可能是不会再回乌克兰生活了。但是战后我们律所很可能会在基辅设立一个办公室,以加强和乌克兰法律界朋友们的国际业务合作。至于乌克兰的生活,当然是很怀念的。有过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以后有空会再多写一点战前普通人在乌克兰的生活。因为这个专栏是自由随笔性质,基本上是想到哪就写到哪,没有固定的章程或者格式。所以这一期打算写一下我自己对乌克兰的最初印象,即个人命运怎么会从西欧中心的比利时,和乌克兰这个东欧国家产生了联系。
佛经里说缘起是,“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缘起,即非缘起,是名缘起。很奇妙的是,我最开始了解乌克兰,竟然是通过一个美国室友。她来布鲁塞尔留学之前,在乌克兰当过两年志愿者,以促进美乌之间的民间交流,最主要的成就是筹款为乌克兰东部乡下某地修建了一口大水井。当时的我孤陋寡闻,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Peace Corps这么一个组织。听了她的经历,看了一些她当时在乌克兰的照片,觉得美国姑娘真生猛。一个年轻女子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国家的穷乡僻野住了两年。室友说乌克兰并不危险,她唯一一次遇到骚扰,是有天晚上她的房东喝醉了酒,想要进入她的房间,但是被她强行驱赶走了。她说,如果他敢乱来,我就让他再也当不成男人。听了这个故事我对室友深感敬佩,这可真是不是一般女人,虽然个头娇小,但是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强悍和勇猛。
总的来说,美国室友认为,一方面,乌克兰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官僚专制而腐败盛行的国家,而另外一方面,人民群众热情友好,善良好客,她在那边结交了不少好朋友。“而且帅哥美女特别多”,室友补充说,“我们和她们相比,就好像丑小鸭一样(ugly ducks)”。我没有想到一向各方面都自信满满的她竟会如此自谦。客观来说,美国室友也还算漂亮,和美剧“国土安全”的女主角有点像,侧面更是神似歌手Tori Amos – 有时候和我说话,她会突然冒出一个俄语单词,加上一头金发,让我不禁怀疑她有俄国血统。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可能已经不知道Tori Amos是谁。她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China”。她的Silent all these years在上个世纪也曾经风靡一时。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原创女歌手。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闲聊美国的约会文化,后来话题蔓延到了乌克兰女性的恋爱观。室友本人并没有和乌克兰男性谈过恋爱,但是她有不少乌克兰女性朋友,所以有一定了解。室友评价道, 乌克兰女人对男人往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当时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一个乌克兰朋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室友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和室友熟悉之后她带我加入了她的朋友圈。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比利时留学的美国年轻人。其中有个女生K也曾在乌克兰当了两年志愿者。不过她是在西部,说乌克兰语的地区。室友去的是东部,所以学的是俄语。她们说最开始是在美国集训,然后又在基辅强化培训了三个月的语言,最后再一一分派去乌克兰各地做各种慈善项目。室友和K有时候说些悄悄话,不想让我听懂,于是她们就用乌克兰语和俄语。这两门语言很接近,她们互相之间可以理解。室友笑道,Jack, 你要学俄语了。不然我和K当面说你坏话你都听不懂呵。
发现这些年轻美国学生总的来说都喜欢社交,聚会,性格直爽,很好打交道。充满朝气和活力,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以及各种政治活动,干劲十足,和欧洲一般年轻人的气质真不一样。当时我有一辆二手的小破车,能够给室友提供一点交通上的方便,所以我们经常一起夜晚结伴去参加她朋友的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聚会。那一段时间,我的英文口语听说能力简直是突飞猛进。。。室友毕业回美国之后我们一直保持有联系,偶尔还有约时间和K一起我们三人视频闲聊。但是后来大家都参加工作之后慢慢联系就少了。所以有一天当我突然告诉室友说,我去乌克兰了。而且整个邮件特意写的是俄语。她很惊讶,有种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感觉。事实上,我第一次去乌克兰是在距今十年之前。那时候尊严革命已经结束,亚努科维奇逃亡去了俄罗斯。俄罗斯则趁机兵不血刃占领了克里米亚。乌东战争已经打响。基辅街头小店到处有印着普京面孔的卫生纸出售。我当时是第一次到乌克兰,事事新鲜,还特意拍了各种普京品牌卫生纸的照片,发给比利时和美国的朋友看。

第一次的乌克兰之行一路上都在临时抱佛脚,听歌学俄语 -当时俄罗斯歌手Polina Gagarina很火。很喜欢她的“Спектакль окончен”, “Шагай” 等歌曲 – 虽然现在在乌克兰朋友面前我已经不再说喜欢俄语歌曲了- 比如说去年我和一个乌克兰朋友聊起流行音乐,我没有多想,不假思索就给她推荐了Polina Gagarina的一首新歌:“НАГАДАЙ”- 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觉得很有意思,词曲皆佳 -而且朋友她来自东部,母语也是俄语- 没想到她回答道,“Jack,我们不能再听俄罗斯的歌曲了”。然后她给我推荐了一些乌克兰的流行歌曲。比如说现在在乌克兰挺火的年轻女歌手Klavdia Petrivn。我向来从善如流。听了之后发现确实也挺不错,而且对提高乌克兰语水平有帮助 -Klavdia Petrivn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创作型女歌手,她的声音也很有特色,充满磁性。我目前最喜欢她的一曲Бережи мене- 可以单曲循环很多遍,百听不厌。记得前不久有天晚上在布鲁塞尔和一些乌克兰朋友聚会。乌克兰人民是能歌善舞的一个民族。印象最深的是当听到Klavdia Petrivn的歌曲之一Знайди мене,大家载歌载舞,场面非常火爆。碰巧这首歌我也熟悉,玩得不是一般的开心。
到了基辅F到机场来接我(F,化名,性别,女;个人情况,不详;工作单位,未知;照片,无)。事实上,我和F也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美国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那天晚上,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难忘 – 那时候我们刚刚结识,完全不熟悉,在陌生的人群中一人拿着一杯饮料站着聊天。她笑着对我说:
“我不是美国人。我没有钱”。
我们进了停车场坐进了车里,她看着我 – 一副仍然不敢置信的模样,笑道:你真的来了。。。
我说,是啊。Варе́ники吃完了。
有这么快吗?Jack,我们才多少天不见啊。F笑道。
– 现在回想起来,F可真是好人。离开比利时的前一夜,还在辛苦地给我包饺子(варе́ники)。做了满满一冰箱。她说,够你吃半年了。
车真不错。我大力赞扬她新买的X5。回基辅后不久她就升职了。我一直觉得F是当时乌克兰少有的现代化人才,年轻,英语好,懂专业,有海外经历,在大公司工作而且作为新一代独立女性,会开车,事业心强,工作努力,力求上进。和我后来认识的另外一个乌克兰朋友A相似,A也很年轻,英文挺好,也在跨国公司工作。她说公司给她配了专车司机每天接送上下班。我当时心想,太厉害了。我在比利时白混了这么多年,不认识哪怕一个有私人司机的人。后来在乌克兰认识的人多了,发现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底是干啥的,一个个都开豪车,有司机,甚至有保镖 (笔挺的西装之下,可能真带着枪)。。。和比利时人相比差别很大。比如说我熟悉的一个比利时知名大律师,一把年纪了,和我一起出去办案,都是他老人家自己亲自开车 – 一辆很普通的大众。当然,一般比利时人也不太讲究这个 – 感觉乌克兰人更注重这些外在的东西。
F的车虽然很好,但是记得从机场到基辅市区路况却并不好。不如中国很多地方的机场高速,也不如比利时。进入市区到处可见很高很旧的筒子楼。很多阳台上也晒有衣服。感觉到处住满了人。让我想起80-90年代国内的一些城市。毕竟在比利时很少看到这样一排排的破旧高楼。但是基辅市中心还是挺漂亮的。看到不少豪车停在路边。给我的感觉是乌克兰毕竟也是欧洲大国之一,虽然国家整体并不富裕,贫富差距可能也有点大,但是有钱人可也真不少。
夜幕低垂,F和我逛街也累了,于是她带我去了一家有名的特色餐馆吃晚饭。具体位置忘了。只记得生意很好,得排队等位。进去之后发现座无虚席,人声鼎沸,一排排年轻女服务员们穿着整洁别致的工作服来回穿梭,场面很是热闹。餐馆占地面积很大,乌克兰民族风格装修,显得既古老又精致。我就像是进了大观园。目不暇接。心想,室友说得真没错,乌克兰人颜值真高啊。不仅服务员一个个打扮得像模特一样,顾客们也大都衣冠楚楚,非常正式。我想,乌克兰人工应该不贵。在西欧基本上没有看到哪家餐馆,能够请得起这么多的服务员 – 那天晚上吃了什么现在反而已经想不起来了。
第二天去了有名的独立广场。客观来说,我游历过的地方不少,所以当时觉得独立广场本身并不是特别壮丽。当然,独立广场之所以有名,也不是因为壮丽的景观。有个妇女捧着一只白鸽走到我面前,把鸽子放到我手上,然后找我要钱。我没太听懂,但是估计应该是这个意思- 因为F立即把她赶走了。在独立广场和F携手漫步,自然而然地聊起了橙色革命和尊严革命。关于橙色革命和尊严革命 –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熟悉 – 都是改变了乌克兰国家命运线的大事。乌克兰朋友们对此的看法也是各有不同。以后有时间会再详细说一下。
比如说F就认为,乌克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西部地区只讲乌克兰语,而东部则讲俄语,两地本身就有语言和文化以及历史上的各种差异,而且还夹在欧美和俄罗斯之间,左右为难,而寡头们之间的斗争更是造成了地区和人民之间的分裂,从而导致了橙色革命,尊严革命,以及克里米亚问题和顿巴斯的战争。我说,你也在比利时生活过。瑞士和卢森堡也都去玩过 –我们这些小国家都有三门官方语言,不同的语言和平相处,国家没有分裂,没有战争。为什么乌克兰不可以给予俄语(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平等的或者是第二位的官方语言地位呢?
这个问题F并没有答案。她不是西部人,也不是东部人,虽然母语是俄语,但是乌克兰语也挺好,而且她也并不太关心政治。我给她的建议是,基辅作为首都应该学习布鲁塞尔,实行双语,包容东西,团结南北,左右逢源。F笑道,等我当市长了就这么办。我说,我把我的拳击手套送给你。反正我现在已经不练了。拳王(市长)已经老了- 不是你对手。
我年轻的时候确实练过一段时间的拳击。报了大班,请了私教,有个东北好友有时候也陪我一起去公园对练,家里还吊了一个大沙袋。F每次来我家,我都会拉着她一起跳绳比赛,然后我们对着沙袋一番花拳绣腿,完全上不了台面,但是玩得很开心,满是美好的回忆。说起拳击,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放弃拳击改打比利时乒乓球低级别联赛,可能是一个错误。毛主席说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乒乓球比赛虽然好玩,但是拳击可能更实用。记得天天打熬筋骨的那段日子,人年轻腰板也硬,身轻如燕,走路有风。有天傍晚路过布鲁塞尔植物园一条人迹罕至的边僻小径,突然冒出两个贼眉鼠眼的小年轻 – 看长相可能是北非人 – 以为我是落单的游客,故意上前无话找话勾肩搭背,应该是想趁机偷东西。我当即毫不客气一把推开,用法语问道,想干啥呢!?- 这俩厮上下打量我,我站在原地不动,心里一点也不慌。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心想,对方只有两人,都是赤手空拳;打了这么久沙袋,正好实战一回。而万一他们有刀,则按照教练叮嘱过的,一个字:跑。沉默对峙了几秒钟,这俩厮没有再靠近,我也就顺势慢慢离开了。
还有一次去火车南站接一个刚刚从国内回来的中国朋友,因为路上堵车晚到了一点,找到地方看见朋友还没来得及和他打招呼,突然间冒出5-6条好汉看上去也像是一帮北非人,把朋友团团围在中间,光天化日之下,其中一人直接动手抢了他的大行李箱就准备跑。我立马一把将行李箱拉住,趁其不备,夺了回来,同时用法语骂了他一句。那厮立即反抢,没有成功。他瞪着我,没有说话。我行李箱在手,也不敢贸然上前,因为这厮牛高马大,电光火石间脑海里闪过在拳馆学过的各种招式,发现此刻竟没有一招用得上,有把握可将其制服。此时这伙流氓见没有快速得手,毕竟周围人来人往,动静很大,就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各自飞快四散跑开了。看上去配合有素,应该是一伙惯犯。朋友心有余悸,满脸是汗,说幸好你及时到了。我说,刚才要是他们一拥而上。咱们双拳难敌十手。估计打不过他们。和朋友商量了一下,因为东西没丢,也就没有去报警。而且心想即使报警了,估计也没啥用,反正都是得自求多福。
我们普通人面对流氓和暴徒,能够全身而退已经不易。将歹徒当场制服并送交官府,是传说中的侠客们才能完成的丰功伟业。在布鲁塞尔我曾亲眼目睹一名说英语的游客因为反抗被打倒在地,满脸血污,几条年轻好汉拿着抢夺而来的财物拔腿就跑,比兔子还快。旁边不少路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敢上前阻拦。而距离案发现场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是布鲁塞尔的众多警察局之一。我想,如果是教练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教练很厉害,有不少实战经验。他年轻时曾经和小流氓街头混战,以一敌十,大获全胜。他说,没有练过搏击的人,往往不堪一击。快速放倒几个,其他人自然就被吓退了。我看着他钢铁一样的身体,心里艳羡不已。

在基辅F基本上每天都会抽空陪我游山玩水。我们去了乡下,郊区,在森林漫步,听山泉奔流。。。第一次的基辅之旅是柔情而浪漫的。事实上,除了在独立广场,以及后来在二战博物馆参观时偶尔有感而发,我们平时很少谈论战争。当时在基辅几乎也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我们在家可以看俄语的电视,在车上可以收听俄语的电台,可以自由播放俄语的歌曲 – 毕竟顿巴斯很遥远。我们都没有去过。F去过克里米亚,但是顿巴斯她也没有去过。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俄乌两国之间的边境领土冲突会一步步逐步演变恶化成为全面入侵基辅的灭国之战。甚至,更严重的是,如同随笔第一篇里记载的乌克兰IT技术员朋友预言的那样,很有可能,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虽然我衷心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也不要发生。
基辅有家意大利餐馆是F的最爱。我和她也一起去过几次。F说她觉得乌克兰人和意大利人挺像。我问,为什么呢?F说,乌克兰人和意大利人家庭观念都比较重,都很注意衣着时尚,工作效率都不高,而且都有Mafia,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乌克兰的黑帮很厉害吗?-这我是第一次听说。美国室友也没有说过。她倒是说过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其实差别不大,不过俄罗斯人更自傲自大一点 – 可能是因为她在东部生活的缘故,对其他地区并不了解。我当时对乌克兰了解也不多,对意大利和俄罗斯也不了解,所以不好比较。但是今天看来,其他方面不说,至少意大利人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和今天乌克兰人的英勇不屈相比,简直是民族特性本质上的天壤之别。
亲历历史乌克兰随笔系列的第一篇发布之后,有捷克的读者留言说,“我身边也有一些乌克兰的朋友,感觉他们身上有很多跟我们想通的民族性格:勤恳耐劳,团体主义大于个人主义,讲人情味”。我对此是很认同的。乌克兰人和中国人真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且我们都有一个俄罗斯邻居。我们都对外英勇善战(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战争)- 而且从历史来看,我们也都经历过沉痛的大饥荒。在基辅时我去过大饥荒博物馆,心里特别伤感和同情乌克兰人的历史遭遇。乌克兰和中国一样,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以农业国家,而且乌克兰有着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黑土地,是著名的‘欧洲粮仓’,结果却是好几百万人活活饿死 -而当时乌克兰一共也只有约3千万人口。所以后来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欧洲议会,都认定乌克兰大饥荒为一次有预谋的‘种族灭绝’。
F其实工作挺忙的。和我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经常是电话不断,有时候晚上回家了还要熬夜加班。有天晚上她对我说,Jack,извини,我明天必须得去公司开会。。。我说,没问题。我正好一个人出去走走。还没有坐过基辅的地铁呢。F笑道,你想去见别的姑娘呵,那可不行。我有个朋友V明天可以陪你到处逛逛。她正好想练英语。然后F又说,V的男朋友为了追她,刚给她买了一辆X5。她明天会开新车来接你。我心想,乌克兰人真豪啊。泡妞动不动就送车。我们在比利时,吃饭一般都是AA制,看电影也是轮流买票。简直不是同一个世界。这让我又想起以前美国室友对乌克兰约会文化的看法。可能乌克兰女性往往更愿意表现出对异性的依赖,而欧洲女性则更为独立。记得以前和一个比利时女生约会,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天晚上我们开车去她家,她的自行车放在我车里。到了地方我把车停好,正下车准备帮忙,却见她打开家门,非常熟练地把自行车单手举过头顶,一口气走楼梯上了一楼 – 不是小型的折叠车,而是正常大小的山地车 – 看得我目瞪口呆。号称练过拳击的我,也不能如此轻松做到这一点。相比之下,F连一桶水都提不起。我们去超市日常购物,她基本上不负责拿东西。

和V的见面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和她就见过那一次,而且后来再也没有过联系,现在连她的相貌和姓名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穿着华贵的貂皮大衣,开着崭新的宝马,显得很气派。她人很年轻,也很有礼貌。我给她送了一小盒比利时巧克力作为见面礼。她陪我在市区到处逛了半天,参观了著名的2012欧洲杯决赛地奥林匹克体育馆。我买了一点小纪念品回比利时送朋友,然后我们去了郊外的一家乌克兰特色民族餐馆吃饭。第一次品尝了著名的辣椒肥肉伏特加。当时她的英语一般,我的俄语也不好,所以我们聊的时候经常得用手机辅助翻译。总的感觉是V和F很不一样,她对于职业/历史等话题兴趣不大。津津乐道的都是吃喝玩乐去哪度假这些事情。V给我推荐了不少乌克兰好玩的地方,可惜离基辅都有点远,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现在回想起来,F对我真是好。我离开基辅的那天她正好感冒了。脸色苍白。我说,我打个车去机场挺方便的,你不要送我了。她不同意,坚持开车送我到了机场。我们在机场找个地方吃了早餐之后,她脸上才慢慢有了血色。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机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等待登机的临别时光。自从认识F之后,我开始自学俄语,开始对乌克兰有兴趣,而且现在又在基辅玩了十多天,走马观花,开始真正初步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战前基辅普通人的生活,忙忙碌碌,喧哗热闹,又岁月静好。F期待下一步的加薪升职,V可能很快就会结婚,欧冠决赛将在基辅举行。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现在的我和乌克兰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各种联系,而当时和乌克兰唯一的联系就是F – 而且这个联系也很不牢靠,随时可以断裂。我们当时的关系是,彼此感觉不错,可是距离挺远,分手舍不得,谈婚论嫁又为时过早。我当时在律所工作不错,不可能到基辅发展。F也已经选择了回乌克兰,前途一片大好,和我聊起未来的职业规划,她自己也是野心勃勃,有许多设想梦想理想,让我想起信長の野望。大话西游里说,世事难料。易经说,履霜,坚冰至。而我们当时都还年轻,说实话,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只是约好了下个月她来布鲁塞尔看我 – 我们当时确实是这么约好的。
现在回看第一次去乌克兰的老照片,亲身游历过的大好河山, 很感叹三年前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可能已经有上百万人战死疆场。据说是二战以来地球上最残酷的战争。而乌克兰也从世界上黑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未爆地雷最多的国家。联合国估计乌克兰有1/4的国土受到了地雷污染。以后的排雷工作需要花费至少几百亿美金而且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战后回归乌克兰的人们,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无尽的废墟和无边的地雷。况且,现在谁也不知道战争何时才是尽头,乌克兰何时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不禁心想,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在另外一个世界,战争是否真的原本可以避免?还是已发生的,则必定会发生?!
而那时什么都还没有征兆。遥远的清晨F在机场给我一个热切的拥抱。临行临别,我在她手心画了个圆,说,等你来。
F轻声笑道,да (好的)。
我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договорились!до встречи!
(意思就是一言为定,一定要来!- 不要让我成为李白说的那样,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F点点头,扬起眉毛,笑道,да, хорошо。до свидания。
– до свидания 类似于法语的Au revoir,德语的Auf Wiedersehen,西班牙语的hasta la próxima或者nos vemos。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并不完全等同于Adiós,不是Abschied nehmen,也不是 прощай。我以为我们将很快在比利时再次会面。十年前的我是如此确定,深信不疑,如同三年前我也曾经固执地认为,俄罗斯绝对不至于入侵基辅那样。
聖經傳道書1章9節裡有說過: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包括我和F的陈年往事,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 有人恋爱有人分开,有和平有战争,人类的历史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千年不断的战争史。但是年轻的我们并没有经验,没有预感也没有答案。在第一期的乌克兰朋友们非正式访谈录里我说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希望乌克兰的朋友们,有勇气且有智慧,而且有力量,可以尽快实现真正的胜利和长久的和平。事实上,我觉得乌克兰人民并不缺乏勇气,而且得道多助,经过战争的磨练和洗礼,有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支持,乌克兰也会变得更有力量 – 最重要的最难得的,很可能将会是智慧。
一个普通人要获得勇气和力量和智慧并不容易。我出国之后也经历过重头再来,十年磨一剑的这么一个人生阶段,学习了不同语言,从法学院毕业,再加上三年实习,然后才正式成为比利时注册律师。算是有了一点知识,但是离智慧还差得很远 – 一个国家可能也同样如此,尤其是乌克兰这么一个年轻的国家,年轻的人民,可能也需要时间,运气,机遇和练历,甚至是磨难,才能真正获得智慧 – 这可比我们普通人面对流氓和暴徒,处境要更加艰险无数倍。乌克兰面对强大的恶邻,应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怎么实现长久的和平,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智慧 – 归根结底,不应该是由某一个领袖,而应该是乌克兰人民的集体智慧- 来决定国家的未来。道德经说,兵者不祥之器。治大国则若烹小鲜。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结尾处也说,“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所以,等待和希望,勇气和力量,智慧和抉择 。。。我们未来将继续和乌克兰朋友们一起探讨政治智慧/历史得失这个话题。
待续。
作者声明:本人并不经营微信号。有空时偶尔写一点,不定期更新。留言一般我是看不到的(除非助理精选并特别推送给我)- 所以一般不会答复留言。
版权所有©️
商业用途转载请事先联系作者以征求许可。
Jack CHEN比利时注册律师
联系邮件 d.chen@avocat.be